半岛APP bandaoAPP 分类>>
半岛体育- 半岛体育官方网站- APP下载坚持文化抗战 唤起民族意识
半岛体育,半岛体育官方网站,半岛体育APP下载

抗战期间,当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战火蔓延至华南,偏居一隅的香港成为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文化桥梁,也成了爱国知识分子隐蔽而坚韧的抗争阵地。在这片被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土地上,一位出身台湾爱国志士家族的作家、学者——许地山,在1935年至1941年执教于香港大学期间,以教育为根基、以文化为武器,构起一道独特的精神防线。这位以笔名“落华生”和散文《落花生》为人熟知的著名作家,既是课堂上的学者,也是秘密抗日活动的组织者;既是抗战文学创作的实践者,也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塑者。这位跨越海峡的知识分子,在殖民地的夹缝中,以文化之光照亮民族救亡的征程。
青少年时期的许地山,亲历了国家破碎的切肤之痛。他在自述中写道:“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安枕。”这种忧愤,不仅源于家族记忆,更来自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深刻认知。比如许地山早期作品《黄昏后》的主角关怀,在甲午战败后心灰意冷,带着两个幼小的女儿避居硇洲岛,没料到该岛竟然又被法国殖民者占领。这个虚构却又真实的情节,正是许地山少年时代目睹列强瓜分中国的心理投射。小说的主角除了深情地思念亡妻,也时刻直面被列强殖民的羞耻和家国破碎的隐痛。许地山满怀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悲愤,有意识地透过历史场景,叙述甲午战争带给同胞们的伤痛,也让读者明白:当一个民族连脚下的土地都守不住时,所谓的避世“安枕”,不过是自欺欺人。
许地山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不仅针对英国。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殖民政策,许地山更是深恶痛绝。1930年,蕉农(宋斐如)翻译日共创建人山川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许地山为其写序。在序言中,许地山掷地有声地说:“我们不要忘记汉族底子孙有一部分已经做了别族奴隶,做了所谓被征服的,做了亡国奴!这一部分中底最大部分便是台湾人!羞耻和悲愤应当时常存在住在中国底任何国民底心里。”在序文中,许地山详细说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没有参政权,也没有平等教育权,并大声呼吁全体中国人民关注台湾的苦难。而为了的抗日力量,许地山在燕京大学期间也秘密参与台籍人士陈其昌、谢南光、翁俊明等人组织的抗日团体,与台湾同仁们共同谋划让台湾回归祖国的路径。
许地山与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等人交情深厚。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他们就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是志同道合的患难兄弟。许地山更与瞿秋白合作,创作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革命歌曲之一《赤潮曲》:“猛攻,猛攻,搥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还创作了爱国歌曲《卫护我中华》,强调要永保先人功业和民族光荣。这些实践表明,许地山的反帝思想已从文化批判升华为行动号召——不仅要揭露侵略者的暴行,更要用各种媒介与渠道,唤醒人民群众的反抗意识。
此时,香港大学登报招聘中国文学教授。许地山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英国牛津大学取得学位,研究领域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与考古学,拥有丰富的海内外学术人脉;而他幼年随父抗日辗转四方,能说非常流畅的英语、粤语、国语、闽南语,在香港教学、生活完全无障碍。香港大学文学院也正需要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来执掌。于是,经胡适引荐,许地山在1935年9月1日抵达香港,前往香港大学就任文学院院长,开始进入香港文化圈。
就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后,许地山做的第一件事是“拆墙”——拆除殖民教育的思想围墙。他考察之后发现,港大的中文教育仍以八股文为主,课程设置脱离现实,学生对中国历史与民族命运缺乏具体的认知。于是,他参照内地高校的课程体系,将传统的中文系拆分为文、史、哲三系,并增设“中国近现代史”等课程。许地山深知单靠自己的课堂无法唤醒民众,于是他利用自己在国际学术圈的影响力,先后引荐陈寅恪、马鉴等知名学者到港大任教,并积极推动港大与内地高校建立学术交流机制。
“保盟”是宋庆龄在香港组建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旨在向海外华侨与国际社会募集物资,支援内地抗战。但港英当局对“抗日”字眼极为敏感,甚至禁止使用“抗敌”称谓(因此香港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全国唯一没有“抗敌”二字的分会组织)。许地山利用自己的学术权威地位与社会关系,多次通过举办茶话会、艺术展等活动与港英官员沟通,消除他们的疑虑,最终促成保盟获得信任,成功开展接下来的抗日活动。
1941年1月,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许地山联合400多个香港的文化人发送电报至重庆国民政府,反对枪口向内。2月1日,香港文化界发表共同宣言,呼吁团结和平停战,许地山第一个在宣言上签名。之后,许地山又撰写杂文批评官员、公器私用,把国防变成党防。在《七七感言》等文中,许地山以“吠家狗”“饕餮猫”隐喻汉奸与腐败分子,呼吁国内文化界应该进行“打狗轰猫”的内部净化,体现文化抗战的尖锐性。凡此种种,都可看出他一心抗日、主张枪口对外的忧愤之情。
比如许地山在香港创作的小说《铁鱼底鳃》,主角雷先生是中国最早的公费留学生,回国后满腔热血却报国无门,只得在割让岛上的外国船坞里隐姓埋名打工。雷先生穷毕生之精力,发明出具有“人造鳃”的潜艇,但怎么都找不到奉献的对接渠道。小说最后,雷先生和他的发明蓝图一起消失在海中。小说中这个有“鳃”的“铁鱼”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许地山通过潜艇发明者雷先生的悲剧,揭露了战时腐败的官僚体系对国防新科技的扼杀,并隐喻只有突破海洋封锁,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这篇小说,被郁达夫转载于新加坡的《华侨日报》,给予极高评价。
如果说《铁鱼底鳃》是对当时中国“硬实力”缺失的反思,那么独幕剧《女国士》则聚焦“软实力”的动员。作品将传统薛仁贵从军的故事,重构为一曲女性参与的抗战动员令。剧本中,深明大义的薛妻柳迎春,成为故事中的核心人物。当丈夫薛仁贵犹豫是在家中种田还是从军时,她立场坚定地表示,国家没有男子当兵万万不成,并以回娘家去施压相逼,展现出比丈夫更高的思想觉悟。通过对故事的改编,许地山动员女子投身抗战,让香港大学女学生会募款支持抗日将士。据记载,该剧排演的票房收入全部捐给内地伤兵,许多女学生看完演出后,更是主动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团。
许地山提倡,抗战时期要写带弹腥味、带汗味的群众文学。除了小说创作和鼓舞人心的抗战历史戏剧,他也创作了大量针砭时局、具有深刻批判意味的杂文。在《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一文中,许地山强调,战争在假英雄的眼光里是一种赌博,但今日我们渴望的是真正的英雄,战争是正义的最后保障,我们应该为正义而战。他还在《七七感言》里痛陈:暴虐日本虽带着王道面具,却具足了畜道的特征。我们除了对外抗日,同时也应该在内部进行自我清理,并呼吁知识分子不可意志薄弱、悲观迷途。《国庆日所立底愿望》指出:我们要自立自强,不要期望有其他人来辅助我们。“靠别人建立的国家,那建立者一样可以随时毁掉它,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别人是绝对靠不住的。”在《今天》中,他强调要好好地清算七七事变的“血账”,尤其是不可依靠外国势力。“我们底命运固然与欧美的民主国家有密切的联系,但我们底抗战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些呼吁振聋发聩,许多观点即便是放在今日,仍具深刻意义。
首先,是重视公共演讲的启蒙作用,以演讲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许地山在港期间举办50余场文化讲座,主题内容包括移风易俗、学术研究、抗战宣传等等。许地山一再强调,在特殊地区办教育要注重民族意识,所以他演讲主题常常紧扣着民族未来以及文化传承。如《青年对于人类之使命》《抗战中文艺写作应取方针》《作家的责任》《中国之命运与青年》,这些演讲主题富有强烈的时代感又能鼓舞人心,尤其是将国家存亡与香港命运紧密结合,破除了“孤岛心态”。许地山批判殖民教育,多次强调“香港与内地血脉相连”,主张香港人不能做孤岛之民,应该与内地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共赴救亡图存之路。许地山的演讲,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兼具学术深度与战时动员性,深受人民群众欢迎。这些在港大礼堂、香港青年会、九龙劳工子弟学校等处举行的讲座,听众既有高校学生,也有码头工人和家庭妇女。
许地山是香港文协的主席,也是中国文化协进会的理事和宣传组主任。以“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协进会在香港举办了“广东文物展览会”。在为这个展览会所写《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的长文中,许地山叙述了英国殖民者如何通过两次战争强行割去香港和九龙半岛南端,以及甲午战争后英国殖民者如何强行租借整个九龙地区。文中也特别揭示了英国强行侵占香港的强盗逻辑,和借以发动第二次战争的亚罗号事件的真相。透过这种有理有据的学术梳理,许地山还原了历史,重构了香港的文化认同。
尽管遇到许多阻碍,许地山仍然奋不顾身地重构香港的文化认同和强化民族意识。1941年,出于对珍贵文献保存的使命感,许地山接受郑振铎委托,协助把港大图书馆建成战时的文献庇护所,以免文物受到战火波及。7月,许地山与郭沫若、茅盾、胡风、巴金等作家联名写信给世界知名作家赛珍珠、罗曼·罗兰、埃德加·斯诺等人,呼吁国际舆论支持中国抗战。信中写道:“我们的抗战不仅是为生存而战,更是为人类正义而战。请用你们的笔,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这封信后来被收录于《国际反法西斯文学通讯》,成为号召海外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文献。
1941年8月4日,许地山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在香港寓所逝世,年仅48岁。临终前,他仍惦记着未完成的文化抗战工作。今天,当我们回望这位跨海峡知识分子的一生,会发现他的抗争从未局限于一时一地。从家族的抗日精神传承,到北平、英美等地的求学启蒙;从燕京大学的课堂,到香港大学的讲台;从小说创作的隐喻,到公共演讲的呐喊。许地山用一生诠释了何为“文化抗战”:不仅是对外部侵略的抵抗,更是对民族精神的唤醒;不仅是对当下危机的应对,更是对未来希望的播种。
许地山对于中华民族必须摆脱外部势力、戒除懒惰、自力更生有着极为清明的警醒。正如他1941年元旦在香港《大公报》发出的《民国一世》所言:“过去的二十九年,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乃至思想上受人操纵的程度比民国未产生以前更深。现在若想自力更生的话,必得努力祛除从前种种愚昧,改革从前种种的过失,力戒懒惰与依赖,发动自己的能力与思想……我们不能时刻希求人家时刻之援助……更要记得援助我们的就可以操纵我们呀!”许地山所强调的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仍是照亮我们民族昂首前行的精神灯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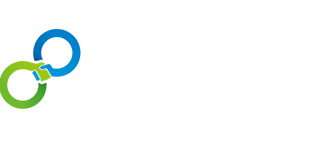
 2025-09-16 23:00:37
2025-09-16 23:00:37 浏览次数: 次
浏览次数: 次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





